在全球能源与原材料市场波动之际,澳大利亚频繁登上世界经济版图的聚光灯——这是一片被自然资源慷慨馈赠的土地。
但资源的富足并非只有荣耀,也可能带来副作用。
在经济学中,这被称为“荷兰病”(Dutch Disease):
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出口高速增长,推动本币升值时,制造业和其他可贸易部门往往会被挤压,导致经济结构失衡。

澳大利亚,正是这一现象的现实案例。
黄金、铁矿与煤炭背后的副作用:荷兰病的历史演变
“荷兰病”并非澳大利亚特有的症状,却频繁在其历史中出现。
早在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,巨量黄金出口曾令澳元(当时是英镑本位)升值,制造业与农业出口受到打压。
此后,澳大利亚又在多个时间点经历了类似情况:
- 1970年代羊毛和农产品价格暴涨,
- 2000年代初至2010年代中期的“矿业超级周期”,
尤其以铁矿石和煤炭出口为代表,构成了最典型的“资源繁荣→汇率升值→非资源行业受挤压”的链条。

特别是在2005至2013年期间,受中国强劲需求拉动,澳元兑美元汇率曾突破1.10的历史高位。
这一时期,虽然全民收入水涨船高,消费火热,但传统制造业出口份额逐步下滑,澳洲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质变。
矿山繁荣,工厂沉寂:制造业如何被边缘化?
澳大利亚储备银行(RBA)在研究中指出:如果没有矿业繁荣,澳洲制造业产出可能会高出5%左右。
看似不大的差距,背后却是就业、技术投资、产业链条的大幅收缩。
2000年后,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稳步下降,目前已不足6%;就业比重也已跌至个位数。这一趋势并非单一由矿业导致,技术全球化、成本优势外移等也是主因。

但矿业的吸金效应不可忽视。在资本、劳动力和政策资源向矿区集中时,工厂逐步退出了舞台。
同时,制造品出口比重从1990年代的20%以上下滑至不足10%。曾经出口日本和东南亚的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,如今几乎被资源品所取代。
2020年代的现实:澳洲仍在“挖矿模式”中
出口结构依赖资源仍是主旋律
根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(DFAT)最新数据,2023–24财年铁矿石、煤炭、天然气和黄金四大资源产品合计出口超3300亿澳元,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超过50%。
其中,仅铁矿石一项就占出口的21%。

制造品出口呢?只占到8%左右。而服务业出口(如教育、旅游)也常受疫情或全球周期影响,难以构建稳固“第二支柱”。
汇率浮动虽缓冲压力,但问题仍存
虽然澳元在2022–2025年间已从高点回落至0.65–0.70美元之间,一定程度改善了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,但相关投资并未明显回流。
原因在于,制造业链条和人力资源已在前期逐步流失,难以快速恢复。
澳洲制造仍面临“高工资+高能源成本+小市场”的三重约束。
不是矿业错了,而是结构太单一
必须指出,矿业并非澳洲的问题所在——它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、创造了高薪岗位,并维持了国家的国际收支。
但正如一台机器不能只靠一个齿轮运转,澳大利亚经济若过度依赖矿业,无论是面对全球需求转向,还是环保趋势变化,都会显得脆弱。
而且,矿业本身波动剧烈:2022–23财年资源与能源出口高达4660亿澳元,但随着全球价格回调,2023–24年预期将降至4170亿,2024–25年预计进一步下滑。

这意味着,仅靠资源来“保增长”,是不稳妥的。
未来该怎么走?让资源成为“跳板”,不是“枷锁”
经济学界普遍认为,解决“荷兰病”不是放弃资源,而是通过以下策略,避免“单腿走路”:
- 设立主权财富基金(如挪威经验):将矿产收益的一部分投入长期产业发展;
- 加大对高端制造与绿色能源的投入,引导资本流向未来产业;
- 打造强韧供应链,通过区域合作布局制造能力;
- 汇率政策保持灵活,确保非资源行业不被“涨汇率”压垮。
结语:资源是财富,也是试炼
澳大利亚的“荷兰病”从未真正消失,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周期中反复上演。
当前的资源繁荣依然在为国家带来可观红利,但代价也显而易见:经济多元化被削弱,制造能力逐渐退场。
真正的考验不是资源是否会枯竭,而是澳大利亚是否能在资源繁荣中,培育出新的增长引擎。
否则,当下一轮商品价格跌落,澳洲或将再次面临“只剩矿山”的风险。
资源盛宴下的隐忧:澳大利亚的“荷兰病”困局
在经济学领域,“荷兰病”一词描绘了一个令人警醒的资源悖论:当一个国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时,短期繁荣往往伴随着货币升值、制造业衰退和长期经济脆弱。
这一概念源于荷兰1960年代开发北海天然气后的经济困局——资源财富涌入推升本币汇率,工业竞争力急剧下滑。

而如今,坐拥全球最丰富矿产资源的澳大利亚,正在这一诅咒的阴影下寻找出路。
1资源繁荣的双面刃:增长与失衡
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创造了现代经济史上的奇迹。据澳大利亚央行研究,截至2013年的十年间,资源产业使家庭人均实质可支配收入增长13%,失业率降低1.25个百分点。
然而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同样锋利:制造业产出比没有矿业繁荣的情景低了约5%,农业也承受着巨大压力。
这种产业失衡在投资热潮消退后更为凸显——随着矿产价格波动,GDP增长从2010年的5.8%连续下滑至2013年的2.6%左右,经济韧性备受考验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资源收益分配的失衡。
悉尼大学教授Matt Barrie尖锐指出:与挪威对石油业征收80%资源税并建立1.4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相比,澳大利亚的矿产财富大量流向跨国公司,国内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未能同步提升。
结果,尽管坐拥全球最大的铁矿石、锂矿储量,澳大利亚2023年制造业占GDP比重仅5.39%,全球经济复杂性指数跌至第102位,甚至落后于部分新兴经济体。
2荷兰病的发病机制:澳大利亚症状解析
荷兰病在澳大利亚的传导遵循经典路径:
汇率通道:
矿产品出口激增推高澳元汇率,削弱制造业出口竞争力。尽管近年澳元有所贬值,但已无法挽回通用汽车、福特等制造商撤离的决定。
资源转移效应:
资本和劳动力涌向矿业,挤压其他产业。西澳皮尔巴拉矿区卡车司机年薪可达20万澳元,远超制造业工资水平,引发全域劳动力成本上涨510。
支出效应:
资源收入增加刺激国内需求,但受益的多为不可贸易的服务业,制造业反而因进口产品竞争加剧进一步萎缩。
更令人忧心的是政策短视。
能源领域出现荒诞局面:
作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,澳大利亚东海岸居民却因国内供应不足被迫进口高价天然气,引发电价飙升。
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才能让普通家庭用上电。
这种结构性缺陷使澳大利亚在算力革命中掉队,AI等高端产业难以立足。

表:澳大利亚资源依赖症的关键指标
3国际镜鉴:从诅咒到奇迹的转型之路
纵观全球资源型经济体,成败分野在于制度设计与治理能力:
失败案例的警示:
非洲国家呈现“坐拥金山却穷如乞丐”的荒诞现实。刚果(金)拥有全球最大的沉积铜矿带和硬岩锂矿,却因战乱频发、基层腐败沦为“投资黑洞”——警察直接勒索中国投资者,移民局见面索贿。津巴布韦则将矿权切割成150公顷的“碎片化”地块,手写矿证导致权属重叠,系统性阻碍规模开发。
成功转型的启示:
荷兰自身提供了最生动的逆转案例。经历1970年代制造业衰退后,政府实施工资抑制政策(三年冻结加薪)、财政重整(压缩政府支出)、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稳定汇率,最终创造连续26年无衰退的“荷兰奇迹”1015。挪威则通过高额资源税和主权财富基金,将石油收益转化为全民福利,成为资源国有化的典范。

表:澳大利亚与挪威资源管理模式对比
4破局之道:澳大利亚的资源转型路径
要打破资源诅咒,澳大利亚需多管齐下:
(1)重构资源治理体系:
借鉴挪威模式,提高资源特许权使用费,建立主权财富基金。当前昆士兰州已开始试点,将部分煤炭收入投入可再生能源基金,但需联邦层面制度化58。
(2)产业政策再平衡:
重点培育三大方向:清洁能源(光伏制氢)、关键矿产加工(锂精炼)、数字产业。需扭转研发投入不足现状——目前澳大利亚研发支出占GDP仅1.8%,低于OECD国家2.5% 的平均水平5。
(3)破解住房-移民悖论:
移民涌入加剧大城市住房危机,房价高居全球前列。需扩大“建设出租”(Build-to-Rent)模式规模,目前在建的7200套住房中,仅10%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,远不足以缓解社会压力5。
(4)劳动力技能革命:
职业教育体系(TAFE)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。悉尼大学教授指出,基础技工短缺已导致“装一台空调收费500澳元”的畸高人工成本。急需与企业合作重塑职业技能标准5。
5从“幸运之国”到“智慧之国”
澳大利亚站在资源十字路口:地下仍蕴藏价值21万亿澳元的矿产,但依赖老路的代价日益显现。
荷兰病的本质并非资源本身,而是治理能力的缺失——当政策被短视政治裹挟、制度让位于投机主义时,金山银山终将化为流沙。

正如非洲问题专家宰纳布·奥斯曼的洞见:“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诅咒。看看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——资源没有阻碍它们发展,但需要为各国提供替代方案”。
对澳大利亚而言,替代方案的核心在于将资源财富转化为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,在资源红利尚未枯竭的窗口期,完成从“幸运之国”到“智慧之国”的惊险一跃。
历史证明,资源诅咒并非无解命题。
挪威将石油黑金变为全民福利基金,荷兰通过结构性改革创造四分之一世纪的增长奇迹。
澳大利亚需要的,是正视繁荣假面下的裂痕,以勇气重塑资源与未来的契约——毕竟,矿藏终会枯竭,唯制度与创新永续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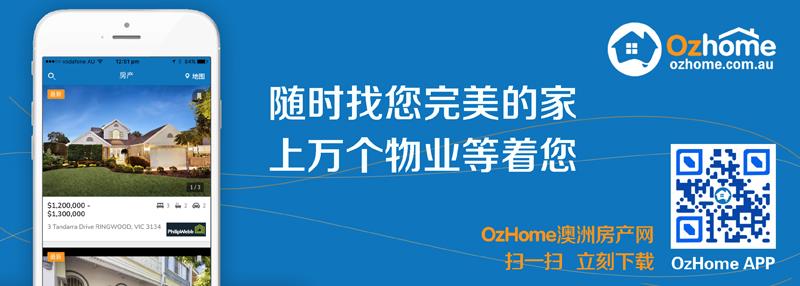
中国有句老话,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但是同时也有一句家训曰:坐吃山空!金山银山总有一天变成空山,能创造财富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生存之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