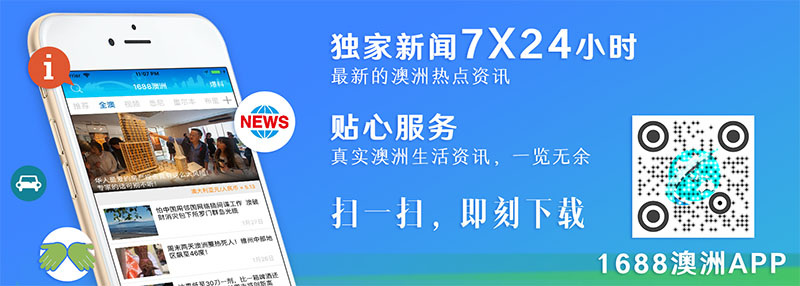我怀念过去那些得“男人流感”(man flu)的美好时光——任何轻微的症状,比如咳嗽、流鼻涕,甚至单纯的不适,都可以夸张地形容为濒临死亡的绝症。
上周,我以为那段日子回来了。
症状很轻,咳嗽、偶尔发烧,然后发冷。可能是男人流感,感觉像是男人流感。
虽不严重,但足以让我倒在床上休息,翻遍流媒体寻找新剧,要求厨房提供补给,并无休止地抱怨。
新冠快速抗原检测(RAT)现在不再免费了,但我一年前买了几盒。本来我已经认定自己只是得了“男人流感”,但当我妻子检测出新冠阳性后,我也不得不拿起棉签,插进鼻孔。
那两道可怕的红线,瞬间浮现。
如今,新冠感染已经没有硬性规定,只有一些模糊的指导方针。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(NSW Health)只是建议有感冒和流感症状的人避免前往医院和养老院,并表示:“目前没有规定要求你自我隔离。”
除此之外,只是温和地建议“待在家里,直到症状消失”。换句话说,随便你想怎么做。毕竟,没人再关心这个事了。
我短暂地思考了一下,感染可能来自何处。但这完全是无从查证的事。
追踪感染源、揪出“零号病人”并在媒体上曝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从身边人的情况来看,似乎最近新冠感染确实不少。我姐夫和他妻子两个星期前也中招了,他们仍然在咳嗽,疲惫不堪,思维迟钝。
官方说法是,新州卫生部门认为新冠疫情正在减弱。
该部门在1月最后一周发布的最新报告称,新冠感染活动“目前处于低水平”。
而在去年12月,新冠感染水平还被报告为“中等”。新州卫生部门依靠实验室检测数据来统计感染情况,但如果很少有人去做检测,他们又如何得知真实情况呢?
数据显示,2024年1月至11月,澳大利亚因新冠感染导致的死亡人数(4507人),几乎是同期流感死亡人数(951人)的五倍。
流感的死亡率变化不大。2019年,流感导致953人死亡。2016年曾出现过高峰,但整体而言,每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数仍保持在1000人以下。这表明,新冠并没有取代流感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。
当然,也有人怀疑所谓的“超额死亡”(excess deaths)是新冠疫苗导致的。
澳大利亚统计局(ABS)数据显示,2024年1月至11月的总死亡人数相比2023年略有上升,但比2022年下降了3%。该机构依赖死亡证明上列出的死因进行统计。
数据还显示,缺血性心脏病(即常见的冠心病)并未出现激增,而癌症死亡人数自202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每年约38,000人。
2024年死于痴呆症的人数为13,623人,与2023年(12,930人)和2022年(13,592人)相当。
糖尿病死亡率有所下降,而肺炎及其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(不包括新冠和流感)导致的死亡人数略有上升。
2024年75至84岁人群的死亡率比2023年下降了2.2%,而其他年龄段的死亡率略高于2023年。
截至2024年9月30日,澳大利亚总死亡人数为141,232人,并在11月30日前完成注册。相较2023年,这一数字增长了2.6%,但相比2022年下降了3%。
从数据来看,2022年死亡率的飙升直接与新冠感染有关。
然而,卫生部门如今对新冠的应对策略却显得谨慎而低调。或许,政府和卫生机构对过去的过度防疫手段感到有些尴尬。
毕竟,那些超长封锁、超市里为了最后一包厕纸大打出手的混乱场面,已经成为遥远的2020年的记忆。
到了疫情后期,为医疗一线工作者强制接种疫苗或许还有道理,但对教师、消防员和建筑工人的强制接种就显得没那么合理了。
疫苗强制令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(这种不信任在疫情前就已存在),还给反疫苗群体提供了更多炒作的空间。
2022年,我在接种第二剂阿斯利康(AstraZeneca)疫苗后几周内首次感染新冠。那次感染的症状轻微,连“男人流感”的标准都达不到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我大概有18个月没接种新冠疫苗了。我隐约记得在2023年某个时候打过一针辉瑞(Pfizer)加强针,但之后就再也没管过这事。
我估计,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不少。很多人不是主动做选择,而是单纯因为懒得去看医生打针。
如今,疫情已经过去,但新冠仍在我们的社区肆虐,而我们似乎已经遗忘,或者说,选择性地忘记了它的存在。